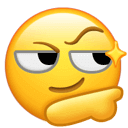那时候,潮起潮落,古镇月芽形码头,常常帆樯如林。搬运工人的号子,美食档的叫卖,充斥沿岸,令古镇弥漫着十足的埠味。
九洲江口的风物,我写过江口渔村,写过江口红树林,现在我想写写江口的船了。
我很熟悉江口的船,因为我家就在九洲江口,就在北部湾畔的安铺古港黄金水道岸边。这里不仅有晨眺江花晚赏落霞的诗情,更伴有云水间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画意。尤其家乡地处江口前沿,是安铺港的咽喉,村头鲤鱼潭河段水深浪静,是来往船舶喜欢停泊和避风的好地方,因此从小我就有机会见到各种各样的船只。

先说说我们渔家的渔舟吧。故乡的船常常浮现在脑际,闭着眼睛我也能把它们勾勒出来:
抛网头船,平头,似古代的战船。浪拍打船头嘭嘭响,一桅一帆,多在浅海作业,以捕捞藻类、贝类和海星为主。这种船已于20世纪60年代被淘汰。
犁头船,头尖,大帆外加一叶三角小帆,靠自然风,速度比平头船快,可出深海作业。合作化时期,这种船比较普遍,成群出没,在海上成了一道风景。
水泥渔船,船体船形与犁头船相仿,用水泥和钢丝制造。吃水较深,最怕搁浅触礁。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主要依靠机械动力。
白条仔,船体很小,形似帆板,船面两侧铺着两块涂有白漆的板,夜间靠水面反照,将趋光的鱼儿诱跳于船上。这种小船最经不起风浪,只选择月朗星稀风平浪静出现在浅滩海角。
长驳,长形船体有点像龙舟。出不得深海,只出没于江河中,在岸与船或船与船之间搞接驳。常常使用竹竿撑船,脚踏船舷,一竿可撑得好远。
竹排船,又称百袋仔,用大通竹组扎成筏,筏面垫高设篷而居。作业时水湿脚,常在江口河滩拉百袋围网。
铁船,多是购置原来一些大公司的二手船,由于价钱不菲,一般是几个人合股。大者好几百吨,出远海捕捞优质鱼。
泡沫船,用泡沫和夹板合成。船体不上油灰,靠泡沫的浮力。造价低廉,一般在浅海滩涂捕捉小鱼小虾。有个时期,家乡泡沫船曾一度发展到近50艘,列泊江岸,颇为壮观,被人戏称为“久渔泡沫舰队”。

忆当年,曾经的黄金水道上,船舶穿梭。江口古镇安铺颇有商埠气势,停泊的船只除了渔船,更多的是商船货船。那时候,潮起潮落,古镇月芽形码头,常常帆樯如林。搬运工人的号子,美食档的叫卖,充斥沿岸,令古镇弥漫着十足的埠味。
如今的江口,由于水利建设和自然的变迁,河道逐年淤塞,更因陆上交通日益发达,江口水上运输也随之萎缩,黄金水道不免变得冷清起来。
追忆黄金水道和船舶的变迁,我曾作过有趣的推论:如果没有百舸争流,江口就成不了黄金水道;如果没有黄金水道,安铺就成不了港口商埠,就难有“小广州湾”“小香港”“广东四大古镇”的美称。船舶成就了商埠。安铺成为通商口岸,成为粤西一个商品集散地,成为享誉一方的岭南名镇,首先得益于早年的江口黄金水道,得益于各条水路的船舶云集。
安铺古港的船舶文化是值得探讨考究的。想当年,靠泊在这里的船舶可谓五花八门:就材质而言,有木船、铁船、水泥船、竹排船、泡沫船;论动力有帆船、机船和机帆船;论功能有渔船、商船、货船和渡船。还有是按地域或渔港来称谓的,如广州船、海口船、越南船、临高船、乌石船、北海船、江洪船等等。无论哪类船,都是船家赖以生存的船,都承载着水上居民的闯海生涯,都在谱写着北部湾的“海上牧歌”。

船舶的今昔反映着历史的变迁。江口船舶文化,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财富。因此有人建议,如果江口黄金水道文旅项目搞起来,别忘了在某家民宿设一个“江口船舶博览”的小型船模展览,以引起人们对黄金水道的浮想,追忆古商埠往日曾经的繁荣,以史为引,提升游兴。
我的童年是在浪尖上摇晃的。祖父的竹排船像片浮动的树叶,载着我在江口星罗棋布的河汊间游弋。那时他总爱指着水面说:"看这江心的漩涡,是龙王爷在清点他的船队。"春汛时节,月芽码头泊满各色船只,桅杆林立如深秋的芦苇荡。晨光里,赤膊的船工喊着"嘿嚯嘿嚯"的号子,将成筐的牡蛎、海带扛上青石板铺就的埠头。咸鱼铺的老板娘支起竹篾大伞,铁锅里煎得滋滋作响的马鲛鱼混合着虾酱的腥香,在潮湿的空气中织就一张看不见的网。

最令我痴迷的莫过于守候归帆。当落日将江面染成琥珀色,各色船影便从海天相接处次第浮现。抛网头船笨拙的剪影总拖着长长的水纹,犁头船的三角帆像展翅的银鸥,而铁壳船低沉的汽笛声会惊起滩涂上成片的鱼儿。祖父能从帆影的倾斜角度判断风向,他说旧时的船老大都懂得看云识天,那些在甲板上晒得黝黑的汉子,心里都揣着本活的潮汐表。
江口的船事里藏着无数传奇。曾有位陈姓船主,驾驶水泥渔船在台风中救起七条人命,自己却永远留在了北部湾的深蓝里。他的船被巨浪拍成两截,船头至今还嵌在红树林的根系间,每逢大潮便发出呜呜的呜咽。还有那支"泡沫舰队",在改革开放初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五颜六色的船体挤满江湾,远远望去像散落的积木。老辈人总摇头说这是"拿命换钱",可正是这些简陋的小船,载着第一代万元户驶向了致富的航道。
月圆之夜,渔人们将船划进银光粼粼的浅湾,船侧的白漆板仿佛两面魔镜。趋光的马鲛鱼不时跃出水面,鳞片在月光下划出流星般的弧线。这时候若在岸边支起吊床,能听见鱼儿"噼啪"落船的声响,间或传来老渔人用雷州话哼唱的咸水歌:"月光光,照船窗,阿妹等郎心慌慌......"
商船云集的年代,安铺港彻夜不眠。来自北海的珍珠船、越南的沉香船、广州的丝绸船在此交汇,码头上方言混杂如同水鸟啁啾。我尤记得那艘临高乌船,船尾总晾晒着成串的鱿鱼干,船主是个满脸络腮胡的黎族汉子,能用树叶吹出《军港之夜》。他的女儿阿月常在船头绣壮锦,五彩丝线在浪涛声里穿梭,织就了多少少年的绮梦。
而今漫步江堤,昔日的喧嚣已沉入时光的河床。废弃的船骸间,招潮蟹在船缝里钻进钻出,藤壶在朽木上筑起白色城堡。偶尔可见老船工蹲在锈蚀的锚链旁抽烟,烟头的明灭里藏着半生波涛。水利枢纽截断了潮汐的脉搏,高速公路取代了水路的蜿蜒,唯有九洲江入海口那片红树林,依然年复一年地吞吐着咸淡水,像位固执的老者守护着最后的船事记忆。

去年清明,我在老宅阁楼发现祖父的航海日志。泛黄的纸页上,褪色的蓝墨水记录着1958年那场特大风暴:"卯时三刻,浪高过桅,与六船共泊鲤鱼潭......"字迹被水渍晕染得模糊,却仍能触摸到当年的惊心动魄。摩挲着那些歪扭的笔迹,忽然明白江口的船从来不只是交通工具,它们是会呼吸的史书,是流动的家园,是北部湾子民用生命写就的海洋史诗。

暮色渐浓时,总爱去新建的船舶博物馆转转。玻璃柜里陈列的船模精致得让人心疼,那些消失的船型在聚光灯下重获新生。解说员说正在筹建实景剧场,要用全息投影再现"千帆竞发"的盛况。我却在想,当电子浪花拍打虚拟甲板时,是否还有人记得真正的海水有多咸?记得老船工脊梁上晒脱的皮,记得渔家女被缆绳磨粗的手,记得风暴来临前甲板下颤抖的烛火?
潮水又涨起来了。月光下,废弃的船骨镀着银边,仿佛即将起航的幽灵船队。远处新修的跨海大桥亮起灯带,车流的光影倒映在江面,与往昔的渔火重叠成时空的蒙太奇。或许这就是江口的宿命——古老的船事终将沉入记忆的深潭,而新的航程,正随着潮汐的律动悄然开启。
我是渔家子弟,自然怀念江口的船。总忘不了涨潮时刻与小伙伴到栈桥码头眺望江口归帆,跃上船与父辈分享耕海丰收的喜悦。是哦,渔家人习惯颠簸的风光,喜爱咸腥的日子。我为自己是北部湾之子而自豪。以至后来每每回乡漫步海岸江堤,对着废弃在九洲江沿岸躺卧于红树林边的烂船旧船,我都驻足行注目礼。因为我知道,它们都即将接受拆船公司的拆卸解体,从而进入家具公司华丽转身,彻底告别与风浪为伍的日子。此刻,在我的心目中,它们的形象是高大伟岸的。它们像是一尊尊从火线撤退下来的老兵,像是一尊尊饱经沧桑的历史老人,像是一尊尊威武的北部湾船夫的浮雕……
啊,故乡江口的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