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人物》与陈婧霏有过一次交谈。当时她的歌手生涯刚起步不久,对很多人来说,「陈婧霏」是沉寂许久的歌坛一个新鲜的名字。后来围绕这个名字,我们知道了那个月亮与六便士的故事——一个顺从原本的人生路径一路奋进的「好孩子」,在生命某个时刻突然惊醒,眼前金光闪闪的人生并不是自己想要的,她任性又决绝地跳下原本极速前行着的人生列车,在旁人错愕的目光中决心重写自己的命运。
四年中,她从北京搬到上海,有了人生第一次巡演,发行了自己第二张专辑,旧世界伴随时间的远去而崩解,新秩序依从她自己的意志慢慢显形,陈婧霏远比从前快乐和坚定。
人生很漫长的一段时间,陈婧霏都在与「他们说」周旋,他们说要乖巧懂事她便乖巧懂事,他们说好好学习上清华她就好好学习上清华,她为此收获过满足他人期待的成就感和虚荣心,她也曾真的以为,这些获得足以撑起自己的人生。
甚至即便是跳下原本的人生列车,「他们说」的阴云也时常弥散四周,他们说任性要付出代价,他们说每个圈子都有自己的规则,他们说,他们说……
而这一次,陈婧霏选择自己说。
四年后,陈婧霏应《人物》邀请进行了人生第一次演讲。她有点儿紧张,但心绪很快平复。一个人要走过多么漫长的道路才能真正拥抱自己,陈婧霏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对陈婧霏来说,过去四年,掌控自己的人生从一种愿望变为既成事实,她发现从前许多的「他们说」都不攻自破,原来做自己想做的音乐、唱自己想唱的歌也没有那么困难,梦想不必通过委屈自己来达成;原来保持幻想是这坚固的世道实在稀缺的美德,她不敢想象如果不是脑袋里那些没完没了的幻想,自己的人生将会是什么模样;原来月亮和六便士也并不天然对立,她拥有了自己热爱的工作,在那些志同道合的伙伴处听到回响,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自己的任性和一意孤行,她同时拥有了六便士和月亮。
这大约是陈婧霏的故事最动人的地方,一个一路压抑自己的女孩决心叛逆,洞察了人生的游戏本质后发愿创造新的游戏规则,扔掉他们的定义,决心把自己的名字变成一个形容词。
以前陈婧霏会疑惑,「他们说」的或许没有错,但「他们」又是谁呢?
但现在相比「他们」究竟是谁,陈婧霏更关心自己最终会成为谁。
以下为陈婧霏的讲述——
策划|《人物》编辑部
大家好,我是陈婧霏。
站在这里的感觉很奇妙,两年前的秋天,我人生第一次巡演的最后一站,就是在这个场地。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女孩,那次巡演像是逃离故乡后终将到来的重逢。离开的时候,关于命运会通往何处,其实自己心里很没有底。那时候我对北京感受复杂,这座城市给我熟悉和血肉,也给我禁锢与痛苦。
我生在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很晚才生下我,年龄的鸿沟多少隔绝着我们,他们是很传统的那种家长,一心盼望我乖巧懂事、稳妥不出错。
但我偏偏从小爱幻想,脑袋里总有另一个世界,小时候偷爸爸的影碟看,电影里的女主角们各个活得精彩,而我却要上学,考试,做题。而命运又偏偏安排给我特别擅长学习的剧本,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扮演着一个符合父母和社会主流期待的那种小孩。
我得到了成就感和虚荣心,但我并不快乐。一直被什么东西困住了。
一路这么角色扮演着上了清华,又申到美国最好的研究生,读的也是热门的经管专业,人生好像一列轰隆隆前行的奋进号列车,在那条轨道上再奋进几年,金灿灿的人生似乎唾手可得。
但我就是觉得不对劲儿,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我加入了学校话剧团,一群爱做梦的年轻人在有限的资源下排练简陋的戏剧,当时大家都愿意演主角,我那点儿叛逆终于派上用场,我更喜欢那些张扬复杂的角色。
到美国留学之后,想象中的自由没有到来。研究生课业异常繁重,地球两端为培养未来精英设置的规则异曲同工,我尝试适应和忍受,但人生就是这样,一旦眺望过另外一种可能,你就没法再继续原本的演出,我演不动好孩子了。
一番挣扎之后,我选择退学,飞回北京面对父母震惊和错愕的目光。当时我铁了心要干艺术,我妈特逗,说你再怎么干,能干得过人家高晓松和周晓鸥吗?其实她给搞错了,她想说的是高晓松和李健,这俩都是清华的。对他们来说,优等生女儿为了发烫的文艺梦放弃大好人生,即使到现在,也是需要深吸几口气才能接受的事。
回家后第一个月过得尴尬又痛苦,从奋进号列车上跳下,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是挣钱。不可能再跟父母伸手,我开始找工作,研究生肄业找工作很尴尬,后来我找了在新东方教英语的活儿,台下齐刷刷渴望登上奋进号的年轻人,那画面很幽默。
干了半年,攒了点儿钱。兴冲冲给很多文化公司投简历,但都石沉大海。父母一看这样下去不行,又催我好歹把研究生文凭拿到手。正好那年伯克利音乐学院西班牙校区新开了一个叫全球娱乐管理的专业,父母对我读什么专业其实也不关心,我用攒下的工资交了学费,飞去西班牙曲线救国。
到了伯克利我才发现,终于都对了。周围都是同类,大家一起自由散漫,一起白日做梦。有回有人问我,会不会写歌,能不能唱中文歌。那时我根本不会写歌,唱歌也是玩儿票性质,登上过最大的舞台是清华校园歌手大赛,在一众铁肺高音的PK中败下阵来,因此也没什么自信。但在伯克利,标准变了,周围人告诉我我唱得比专业歌手还要好,因为专业歌手唱得太完美了,完美,但没有辨识度,没有人味儿。
人生第一次,不是因为成绩好,不是因为符合什么标准或达到什么水平,而仅仅因为「我是我」而被认可,这种被看到的感觉让我特别开心。我也搞清楚了内心一直以来别扭的是什么,所有的困惑和不对劲儿,所有的打不起精神,都是因为我不能成为我自己。
大约从那时开始,真正的陈婧霏才慢慢苏醒。我学着写词,日子一下子充实起来。毕业后回国,我进了一家音乐公司上班。上班间隙把自己翻唱的歌儿传到网上。后来有机会参加比赛,比赛要求原创,我又学着写曲子。
之后的日子开始加速,我有了第一支自己创作的单曲,收到一些不错的反馈,写歌的乐趣盖过生活里所有事,音乐公司朝九晚七还挣不到什么钱的日子失去意义,我就又回到新东方教英语,攒一阵工资做一首歌,日子窘迫又迷茫,但终于有了一些快乐。
2020年,我出了自己第一张专辑,专辑名字简单粗暴,就叫《陈婧霏》,对我来说,这张专辑是那个时期理想自我的投射,是我人生想要活成的电影,是我为自己造的梦。我终于可以在创作里,扮演一次自己渴望成为的「陈婧霏」,而我,是这部电影里唯一的主角。
那之后开始全国巡演。时间来到两年前的这个空间,我回到北京,在灯光和音符织造的舞台上,对着台下的观众说,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着这座托举我也羁绊我的城市说,「hi,我是陈婧霏。」
时间又过了两年,与此时此刻的我在同一地点会和。
这种感觉挺命运的,让我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自己人生故事的更多局部和细节。
去年年底,我发行了第二张专辑《猩红》,相比于首张专辑时的生涩紧张,现在的我已经进化得更加自信和坚决。我总开玩笑说,两张专辑隔了快四年,我感觉用的都不是同一个脑子。
第一张专辑没有任何宣传,整个人就有很多不确信,甚至有点儿自卑,更准确的描述是又卑又亢,一方面对自己的审美和潜力有种狂妄的自信,一方面又因为内心的恐惧脆弱四顾茫然,很长一段时间我听不到反馈,石子投入水面没有声响,那种安静一度让我无比慌张。我走上的是正确的道路吗?谁会支持我呢?很多患得患失的情绪。
驱散这种情绪的依然是时间。回声虽然缓慢,但陆陆续续从四处传来。像是一场减速又加速的魔法,这些声音随着时间汇集震荡,给了我越来越多确信和力量。更重要的是,我得到了那些我欣赏的人的认可,那些我默认的同类,那些跟我一样沉迷于幻想和创造的人们。
去年10月,我收到了邵艺辉的短信。小邵同学诉求直接,「婧霏愿不愿意给我们的电影写首歌。」
「妈呀我可太愿意了。」我是《爱情神话》的粉丝,喜欢小邵那种与生俱来的轻灵。10月末我看了《好东西》,我相信你们后来肯定体验到了和我同样的激动,我看到了真正的「好东西」,一种理直气壮的新,新的游戏规则,新世界的召唤,一切都是新的。
创作时间只有一周,灵感在看到茉莉作文《我不再幻想》时开始闪动。我当然会想到自己的小时候,正直勇敢阅读量一般,但嘴欠爱幻想,敏感又脆弱,觉得自己很特别。我想茉莉是每个女孩的过去,也寄予着每个女孩所憧憬的未来,而在这世上我能想到对一个女孩最美好的祝福,就是祝愿她拥有成为自己的自由。
我把这首《她不再幻想》当作铁梅对茉莉想说但没在真实世界说出口的话,其实也想借铁梅之口,期望身边每一个「茉莉」 、每一个你我她,都能更勇敢地创造自己的游戏规则, 纵情活出内心真正的渴望。
整首歌里我最喜欢的两句是,「不追求谁会怜奖,不祈求谁能体谅」,相比于刚起步时那个总期待回响的自己,虽然现在还不能完全做到不在意外界的怜惜和认可,但我知道,这两句歌词是我要去的方向。也是跟这些美好的创作者们并肩站在一起的过程中,我的内心慢慢趋向于一种不卑不亢,我对自己的创作、对陈婧霏是谁越来越确信。
创造这份确信的是一则来自时间的谜语。2021年,我在杭州单向空间参加了一次对谈,具体细节已经模糊,但我永远记得对谈中的某个瞬间,一个句子在我脑海炸开:我只想把「陈婧霏」变成一个形容词。
回到当时,这句话更像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虚张声势的宣言。但从这开始,我和自己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改变,在此之前,我一直过着一种被定义的人生,不管是已经逃离的原本的生活,还是后来被称为歌手、唱作人,统统来自外界的某种设定。但在这个时刻之后,一个念头变得愈发猛烈,为什么我不能定义我自己呢?
这个时刻之所以特别,是我终于意识到,对一个女孩儿来说,她要经历多少抑制、否定以及自我否定,要听过多少不行、不应该、不可以,要承受多少我是为你好、你得听我的之后,才能在旧世界的迷雾中找到真正的自己。
在这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刚进音乐圈的时候,身边老有声音说,你得去社交,得多认识人。刚开始我也不坚定,也很害怕失去所谓的机会,会硬着头皮去当一个局中人,但每次都感觉很消耗。慢慢地,我发现我所有的机会,都是拿自己的创作挣来的。后面再有类似的邀约,我学会了拒绝。学会拒绝简直太爽了,开始还假惺惺地找理由,后来干脆直接说我不想去。
更直观的改变在创作上。
我觉得我真正在这个世界上最想做、最擅长的,就是把我自己表达到极致。像大卫·鲍伊脸上的那道闪电,像草间弥生幻化出的波点,无论是通过声音、文字还是影像,或是别的什么媒介,我都希望这件事的终途,是把「陈婧霏」变成一个形容词。我希望在久远或不久远的时间之后,陈婧霏可以抽象为一种感受,可以是浓烈的色彩、迷乱的光影、油画感的幻梦,或者是沉浸或颤抖。
正是涌动着这样的野心,我发行了我的第二张专辑《猩红》。给《好东西》写配乐的那段时间,正是《猩红》制作的尾声。时间到了这里,我已经进化成了理想中的自己。纯真和放荡并行于我的脑海,小女孩和大女孩的自由同样让我激动。我想新世界之所以无边宽广,是因为在我们憧憬的新秩序中,每一个小女孩的幻想都应当被呵护,每一个大女孩的欲望也应当被正视。
《猩红》是我脑海中的十幕时空戏剧,某种意义上我又回到了清华话剧社从未真正落幕的舞台上,继续扮演那些张扬复杂的角色。旧世界的脚本中,作为一直被观赏的对象,女性的野心和欲望总是伴随着否定和凝视,但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定义自己呢?于是红发的女巫是我,北海的水妖是我,天真的是我,放荡的也是我。在这一幕幕的戏剧中,我不卑不亢,为我是我自己由衷骄傲。
我想这是身为创作者最大的幸福。少女时代发了疯地幻想,终于可以借由创作一次次成为现实——走过那么漫长的路,我终于成为小时候那个「好小孩」的完美镜像,并在时空交错处给她一个深深的拥抱,告诉她不要停止幻想,你是最特别的小孩,你会长成你想成为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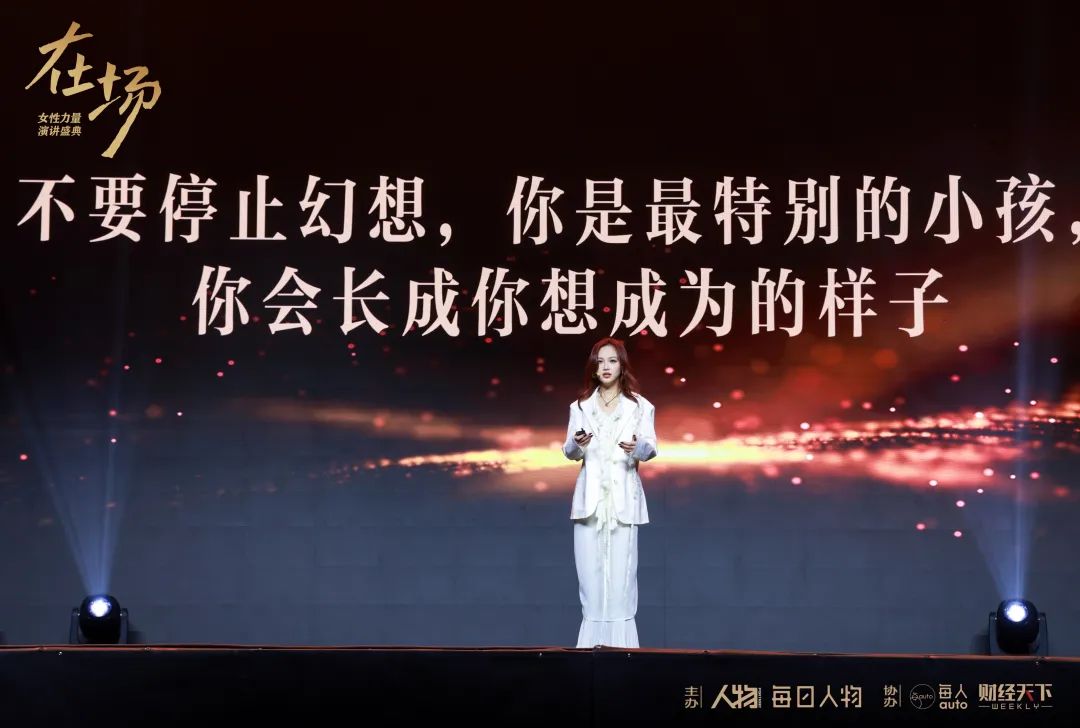
时间所限,这就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故事了。
讲到最后好像还没有点题,关于在场,我一直把人生看作一座巨大的游乐场,我们身处其中,投入我们的游戏。前阵子Deepseek大热,AI接管人类简直就在眼前,有些天每天早起,我都会调戏一下Deepseek,有回我跟它说,用陈婧霏的风格给我写首歌,它「思考」了一会儿,发来一段歌词,我一看两眼一黑,太油腻了,难道在AI眼里我就那么油腻吗?但是那天我却很开心,我想正是因为爱和欲望的不可复制,正是因为我们的感受和不完美,我们才是我们。
结束今天的夜晚,我会回到我的游乐场,继续为把陈婧霏变成一个形容词努力。愿你们也为成为自己而努力。
我们在新世界相见。
亲爱的读者们,不星标《人物》公众号,不仅会收不到我们的最新推送,还会看不到我们精心挑选的封面大图!星标《人物》,不错过每一个精彩故事。希望我们像以前一样,日日相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