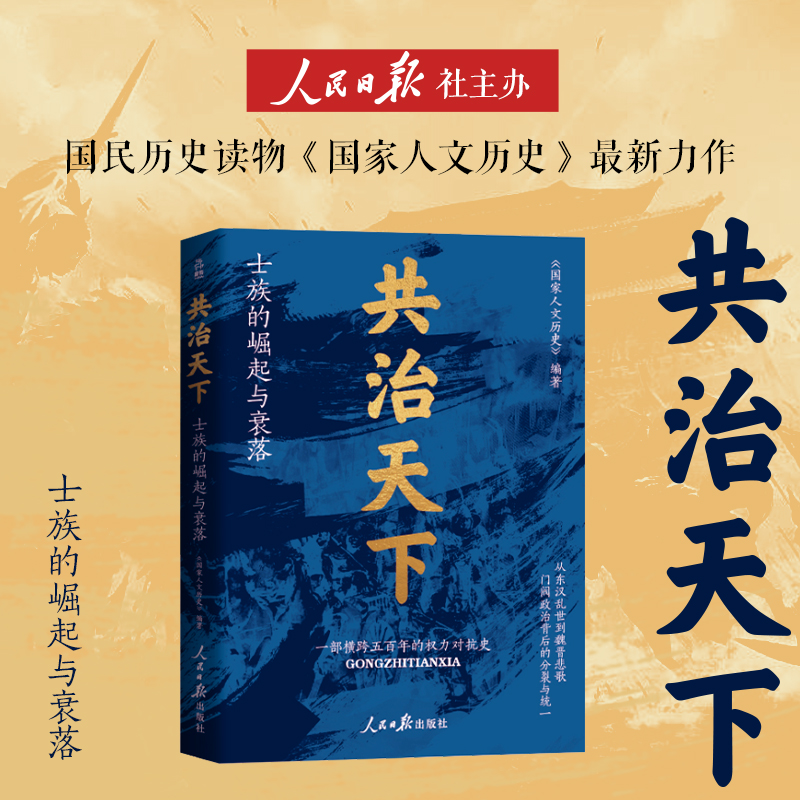20世纪7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乾陵陪葬墓群的考古勘探中,意外发现了章怀太子李贤墓的墓道轮廓。这座沉睡千年的唐代墓葬虽经多次盗扰,仍出土了六百余件陪葬品,墓室中发现的五十多组彩色壁画面积达400余平方米,可以说,这是出土壁画面积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唐代墓葬。壁画的内容涵括了狩猎出行图、马球图、仪卫图、内侍图等多种题材,其中一幅展现唐代外交盛况的壁画《客使图》中,既出现了身着广袖长袍、头戴高大笼冠的唐朝官员,也出现了高鼻深目、秃顶卷发的“异域来客”,这在历朝的墓葬壁画当中,都是极为鲜见的。
那么,墓葬的主人——章怀太子李贤是何许人也,他的随葬壁画当中,绘就了怎样的唐朝外交风云?
“种瓜黄台下,瓜
熟子
离离
”
章怀太子李贤的一生
上元二年
(675)
,长安城大明宫的含元殿内,唐高宗李治正为太子李弘的暴毙悲痛欲绝。这位被武则天寄予厚望的长子,在陪同帝后巡幸洛阳时突然薨逝。然而,储君之位并未因此空置太久,时年22岁的李贤被匆匆推上风口浪尖,命运从这一刻起被卷入复杂的宫廷斗争之中。
李贤是唐高宗第六子、武则天次子,史书中曾数次出现其行为端方、品性高洁的赞语,如《旧唐书》所载:
“时始出阁,容止端雅,深为高宗所嗟赏……处事明审,为时论所称。”
《新唐书》也称李贤“容止端重,少为帝爱”,担任监国处理政务时,则“于处决尤明审,朝廷称焉,帝手敕褒赐”。

据记载,李贤几岁时就能够“读书一览辄不忘”,高宗李治也曾颇为骄傲地对司空李勋夸赞儿子李贤的聪慧:
“此儿已读得《尚书》《礼记》《论语》,诵古诗赋复十余篇,暂经领览,遂即不忘。我曾遣读《论语》,至‘贤贤易色’,遂再三覆诵。我问何为如此,乃言性爱此言。方知夙成聪敏,出自天性。”
成为皇太子之后,李贤召集当时的七位学者共同修订校注《后汉书》,形成了今称为“章怀注”的《后汉书》注本,以其内容广博、注释详密而著称,为后世研究《后汉书》提供了重要史料,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与校勘价值。李贤的政治才能与文采学识,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在皇帝赞扬、朝野称颂的表象之下,太子李贤的政治危机正在悄悄酿就。
谣言来自宫人们的悄声议论,说“贤是后姊韩国夫人所生”,也就是八卦李贤并非皇后武则天亲生,而是武则天的姐姐韩国夫人所生。但是李贤出生于永徽五年
(654)
十二月,当时的武则天尚未封后,她的姐姐自然也没有进宫受封,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谣言。但这个关于太子身世的秘闻口口相传,甚至见载于史书之上,可见其在当时流传之广,以至于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即李贤坐上太子之位的正当性。这
是李贤政治悲剧乐章的第一个小节。
如果说前一个谣言尚且可以不攻自破,另一个谣言就要严重得多,也更让太子李贤感到惶恐与惊慌。当时的正谏大夫
明崇俨
以医术和符咒幻术见称,因其能够驱使鬼神、治疗疾病而“入阁侍奉”,受宠于唐高宗和武则天。明崇俨说太子的弟弟英王“貌类太宗”,又说太子的另外一个弟弟“相王相最贵”。玄武门之变殷鉴不远,皇室手足兄弟之间政治竞争何其残酷,对于太子李贤而言,这种负面评论当然难以接受。不久,明崇俨就“为盗所杀”。
明崇俨之死的真相,今时今日已不可考,但比真相更为重要的是,武则天将明崇俨之死归罪于太子李贤,并以此为契机,“遣人发太子阴事,诏薛元超、裴炎、高智周杂治之,获甲数百首于东宫”。李贤由此获罪,被废为庶人,他的政治生命至此宣告结束。
文明元年
(684)
,武则天派左金吾将军丘神
勣
(jì)
前往李贤的流放地巴州,也许是丘神勣主动,也许是武则天授意,李贤最终自杀。
章怀太子李贤悲剧的一生至此走到终点,1300多年以后,尘封已久的墓室悄然打开,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色彩斑斓、笔意灵动的多幅壁画。
“九天阊阖开宫殿,
万国衣冠拜冕
旒
”
壁画中的盛唐外交史诗
古人推崇“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墓葬作为逝者的安息之地,承载着人们对逝者延续生前生活的深切期望。在营造墓葬时,人们不仅精心打造地下空间,力图还原逝者生前的舒适生活,彰显他们的身份与排场,在细节处理上更是细致入微,不乏奇幻丰富的创造。然而,受限于环境、选址等现实条件,墓葬在表达复杂观念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人们对于死后世界的想象与表达,大多挥洒于墓室的壁画当中。

不同历史时期的墓葬壁画有其各自的艺术特点和表达方式。汉代神仙思想盛行,人们希望死后可以魂魄长存,在墓葬中涵养精气升入仙界,因此,汉代墓葬壁画中将墓主人生前的现实生活与死后向往的神仙世界合二为一,日月星辰、珍禽异兽、神仙出行以及东王公西王母传说故事是
汉墓壁画
的主要意象。
魏晋至隋唐,宴饮、仪仗场景成为壁画主流。达官显贵的墓室里,绘制着规模宏大的宴饮图,宾主觥筹交错,侍者往来穿梭;出行仪仗图里,浩浩荡荡的车马队伍、威风凛凛的护卫随从,极力展现墓主人尊贵的身份和显赫的地位,侧面反映出当时严格的等级秩序。晚唐至宋元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文化兴起,人们的生死观和丧葬观念发生显著变化。此时,人们既不想怀着惆怅的心情步入仙境,也不再满足于单纯对礼制的追求。他们希望在死后的世界中延续生前的美好生活,享受歌舞升平的愉悦。


章怀太子墓的壁画是唐代墓葬壁画中的典例,五十多组壁画以还原逝者生前生活的宏大气象为主题,墓道东壁由南而北依次为青龙图、狩猎出行图、客使图、仪卫图,西壁依次绘白虎图、马球图、客使图、仪卫图,既有描绘章怀太子生前恣意纵马、野外狩猎的闲适生活画面,也有其生前作为储君的权力叙事构图。其中,客使图作为目前我国保存的唯一一幅反映外交题材的唐墓壁画,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
《客使图》高1.85米、长2.47米,主要描绘的是唐朝与四邻邦交来往的场景。画面一共出现了六位人物,前面三位身着唐代朝服,头戴介帻、笼冠,身着红色广袖长袍,腰系绅带,手持笏板,足登朝天履,呈三角状站立,神态威严肃穆,似在商量有关客使外交的具体事宜。关于这三个人的身份,根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分析,一般认为是唐鸿胪寺卿、少卿。卿为鸿胪寺正职,设一名,“掌宾客凶仪之事,领曲客、司仪二署,供其职务”。少卿为副职,设两名,“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辨其等位,以宾待之”。

画面中另外三人为异域使者。紧挨着唐代官员的使者为秃顶、卷发、深目高鼻,身穿翻领紫袍,一种观点认为他是来自东罗马的使节,史籍记载其风俗“男子剪发,披帔而右袒……俗皆髡
(剃发)
而衣绣”。站在中间位置的使者身穿宽袖短袍,脚蹬黄色尖头皮靴,头戴尖冠,帽子上插着两根羽毛,两颊有羽冠束带结于颌下,学者推测其为日本使者或者新罗国使节,据《旧唐书》记载:
“(高丽人)衣裳服饰,唯王五彩,以白罗为冠,白皮小带,其冠及带,咸以金饰。官之贵者,则青罗为冠,次以绯罗,插二鸟羽,及金银为饰。衫筒袖,袴大口,白韦带,黄韦履。”
站在最末位置的使者腰束黑带、身披大氅,两手交握拱于袖中,一般认为是古代东北民族室韦族或靺鞨
(mò hé)
族的使节。
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使者面貌与衣着各具特色,神态栩栩如生,笔触写实细腻,使得《客使图》成为盛唐时期万国来朝盛世气象直观、形象的体现。唐朝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国力被域外各族视为上邦,各国使臣纷纷来朝,进贡通好,与唐朝保持密切的友好关系。据《唐六典》记载,唐朝曾与三百余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外交,每年接待的外国使节、商旅及国内少数民族代表络绎不绝。长安城特设鸿胪寺与礼宾院两大外事机构,专门负责接待各国来宾,国子监更开设国学六馆,为日本、新罗等国留学生提供系统的汉学教育,“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于是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
唐朝通过外交、文化、军事等不同方面的多元手段,构建起以长安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吕留唐五十余年,官至左散骑常侍;波斯王子卑路斯客死长安,被追封为左威卫将军。大唐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接纳着突厥的胡旋舞、粟特的商队文化、印度的佛教艺术,使长安成为多元文明交汇的国际化城市。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东起长安,经中亚五国、伊朗高原、两河流域延伸至地中海东岸,形成长达6440公里的国际商道网络,最终抵达东罗马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
(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这些史实与壁画相互印证,共同诠释着王维在《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中描绘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景象,呈现出“百国同欢”的外交盛况。
站在乾陵之巅,望着章怀太子墓前的翁仲石像,历史的回声穿越千年。《客使图》中的外交使节早已化作丹青,但其承载的开放包容精神却永远鲜活,这或许就是《客使图》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参考书籍:
《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孟宪实著《孟宪实讲唐史·唐高宗的真相》,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美]巫鸿著《中国绘画:远古至唐》,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上海博物馆主编《壁上观——细读山西壁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进击的士族
旁落的皇权
跨越五百年的权力对抗史
国民历史读物《国家人文历史》专业团队
最新力作
展现士族潮起潮落的史诗级历史画卷
↓↓↓